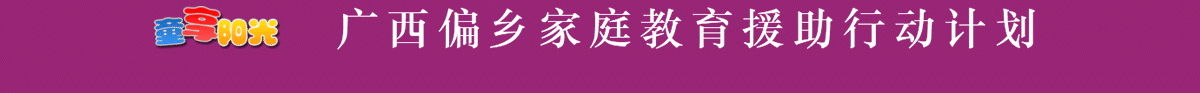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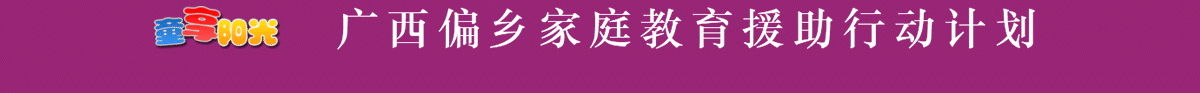
2016-05-27 09:00:21 来源:人民网
在北方一个村的留守儿童资助项目上,社会爱心人士带来很多新书包。在教室里,校长讲述爱心人士的故事,接着对学生们说,你们谁是留守儿童,站起来。给你们发书包!
没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这让校长很生气,叔叔阿姨大老远给你们送东西,怎么谁都不配合了,这么没礼貌。
那时,这些孩子一定在想,“我长这么大,还不知道自己还有个标签叫‘留守儿童’”。
这是中国儿童中心科研与信息部副部长朱晓宇,在昨天举办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模式研讨会暨“光彩爱心家园-乐和之家”试点项目总结会上讲的一个小故事。
在朱晓宇看来,这样的案例造成了对于留守儿童的二次伤害,导致“好心办坏事”。
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近年来,不少社会机构通过各种方式为留守儿童提供关爱服务,尽管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也出现了很多供需不对称的情况,甚至出现对留守儿童二次伤害的现象。
不少与会的专家和相关工作人员都表示,除了这种言语伤害外,不周全的准备工作也会使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变成负担。
据一名社工的讲述,在重庆一个村的关爱活动中,爱心人士准备为一个寄宿学校的留守儿童包饺子,为此,学校暂停了中午免费午餐的供应。然而,他们对学校情况和学生数量不了解,导致每个学生只吃了几个饺子,只好饿着肚子继续上课。
如何对留守儿童进行切实有效的关爱服务,已成为有关部门和公益组织都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对此,中国社会工作学会执行秘书长邹学银认为,在关爱留守儿童活动方面,社会工作组织大有可为,关键是了解当地需求,结合好当地资源。否则,“人力、物力的大量消耗不一定能起到好效果”。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保护处处长杨剑也认同专业社会工作者的重要性。“近年来出现的极端事件,都是因为对留守儿童心理关爱的缺失。”
在重庆市委党校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谢菊看来,不管是官办社会组织,还是一般的社会组织,在进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时都要学会“与当地政府和民众打交道”。
“社工组织要学会协调各个层面的基层政府关系。”谢菊表示,除此以外还应学会和村委会打交道。“他们了解情况,社会组织进入后如果不能与村委会建立良好关系,即使表面上进到村子里,实际上也没进去。”
此外,很多社工组织都是通过项目机制提供关爱服务。“应该明确项目退出机制。如今的项目里面有很多理想化的东西,有的项目退出之后把这些孩子搁半道了还不如之前不干。”朱晓宇说。
一些机构和公益组织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工作体系,值得借鉴。
以“光彩爱心家园-乐和之家”为例,该项目从动员当地社区留守人员的互助体系出发,利用社区内部资源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据项目创始人、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介绍,3年来,乐和社工从社会建设入手,服务了重庆市10个村近3000名儿童,服务范围也延伸到留守妇女和空巢老人。
但是,不少专家及相关工作人员提醒:如今,人们都在讨论社工组织如何帮助留守儿童,却忘了强调留守儿童父母及家人的责任与义务。毕竟,留守儿童问题,归根结底是家庭的问题。
邹学银在广西农村调研的时候曾见过一户人家,父亲常年在深圳打工,他会定期与女儿视频交流,然而每次说个三五分钟,父女俩就没什么话可说了。但每次回来看望女儿,他们聊几个小时都说不完。
“家庭的团聚,家人的沟通往往比社工的帮助更有效,而这些效果也是社工怎么做也比不了的。”邹学银说。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教研室主任郭伟和则认为,当下留守儿童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家庭贫困问题,而是家庭照顾体系问题。
郭伟和指出,在目前的发展趋势下,留守儿童的照顾体系和保护体系的破碎,产生的社会后果可能是个体人格的扭曲和本土文化的自我贬低。
“进一步发展下去,这些孩子就会发展出两种不良状况:一个是自我绝望和自我伤害,也就是毕节儿童自杀案例的表现;另一个是对社会的愤懑和反抗,也就是最近几年日益增多的暴恐袭击或者有组织犯罪现象。”
因此,郭伟和认为,留守儿童的援助目标需要改变,由物质援助导向转向社会服务导向。他说,面对市场化大潮的冲击导致的家庭风险,社会工作的专业判断不能仅仅瞄准个人提供福利救助和安置照顾,而是要把个体补救和社区关系的重建结合起来,让这些脆弱群体有一个社会参与和社会融合的环境和经验,以避免社会排斥导致的边缘人格。
郭伟和强调,目前留守儿童更需要的是,政府通过精准的扶贫策略结合专业社会工作来评估需求、设计服务和提供服务。